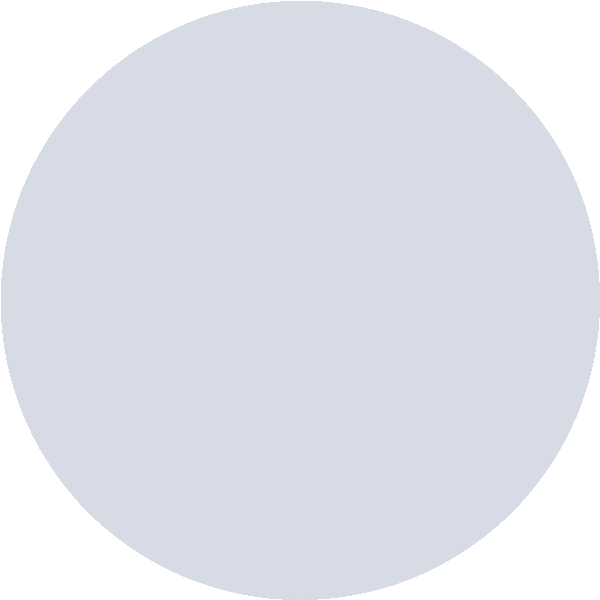💡摘要💡
非传统共识投资:规模 5000 万 - 1 亿美元的传统种子基金,需开展非传统共识投资,关注非传统背景、创业失败及被主流机构忽视的创业者,以及新市场早期和旧市场的非共识项目。
二次创业者更易成功:首次创业成功的创业者易傲慢,创业失败后二次创业的创业者对成功更渴望。
起步市场规模会被突破:优秀创始人能开拓市场,公司起步时目标市场总规模并非关键,像 Media Radar 就突破了最初对市场规模的预判。
要有耐心和坚持:如果觉得自己的某个 portfolio 真的有很深的护城河,那就要有耐心,坚持不卖股份。
本文根据 20 VC 的访谈录进行了编辑
Harry 00:28
这里是《20 风险投资》节目,我是 Harry。今天我非常兴奋地邀请我的一位挚友来到节目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种子轮投资人之一,大卫·弗兰克尔。大卫是创始人集体公司(Founder Collective)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这家公司参与了优步、酷澎、艾可表格、Whoop、Pill Pack 等众多市值达数十亿美元的超棒公司的种子轮投资。

Harry 03:49
我们看到了一些项目种子轮就融资比如 600 万到 1000 万美元。那么规模在 5000 万到 1 亿美元的传统种子基金,要如何在这个新环境中立足呢?
David 04:06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去做非传统共识投资。
那些非共识的创业者,比如来自二流学校的人。那些主流机构不太会支持的人依然大量存在。坦率地说,那些创业失败过、表现不佳的创业者,以及那些被“抛弃”的创业者,主流机构一般不会关注他们。
但我常常想,“非共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如果你在新市场发展的早期就进入,比如当大家都去投资 DTC 的时候,你去投资以太坊,那就是非共识投资。
还有在旧市场进行非共识投资。
我目前担任董事的一家投资组合公司,叫 Smalls,是做猫粮的,我它当前业务良好,它的年度经常性收入(ARR)有 5000 万美元,可是 12 月的时候去融资,根本没人理我们。因为大家不喜欢猫,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非共识投资。

Harry 06:20
你会看到这些项目的定价也会相应调整,对吗?
David 06:22
确实会。我是说,市场还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我觉得如果你还想着“我想要 400 万美元的预估值”,那可就完全不合时宜了。我认为市场有一个清算价格,该付多少钱就得付多少,但这些不是人工智能项目的价格。这可不是那种我出 500 万美元占股 20% 的人工智能项目,那种太不可思议了。接下来你知道吗,我参加了一次视频会议(Zoom),对方在旧金山的一个酒店房间里,我结束会议后对同事说:“我们没戏了,这个项目的预估值会达到 1 亿美元,这是真的。” 顺便说一下。
确实是这样。当下的市场有它自己的一套规律,以前一个估值 400 万的项目现在可能估值 1 亿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放弃投资。
Harry 09:08
有没有过你没有打破规则,保持了原则,却后来感到后悔的情况呢?
David 09:18
你知道,确实有过一些情况,我们出于充分的理由没有打破规则。
David 09:22
我首先想到的是Pinterest这个项目,创始人找到我们,但我们存在利益冲突。我们有一位非常得力的同事,扎克·克莱因,他是 Supply 公司的董事长,我们之前投资了 Supply 公司,所以无法投资 Pinterest。

Harry 09:54
如今,没多少基金能遵守不投资(存在利益冲突项目)的规则了。
David 10:00
在这方面我们非常传统,非常守旧。
Harry 10:02
大卫,你多快能判断出一家公司不行呢?
实际上我觉得很快,我想说大概在前三个月就能判断出来。
David 10:13
跟你说,有些公司我打从一开始就不看好,特别是企业服务领域的。那些公司销售周期长得离谱,让人忍不住怀疑:“这能成功吗?” 就拿 Olo 这家公司来说,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我还没成立创始人集体公司,我跟我妻子吐槽,说投给 Olo 的钱估计要打水漂了,觉得那个诺亚(应该是 Olo 公司的人)根本做不起来。
可谁能想到,每次都以为他要 “凉凉” 了,他却总能融到钱,我一度觉得他是在忽悠投资者。不过后来我也明白了,有些业务确实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成功。
消费领域就不太一样,反馈来得快。哈里,我遇到过不少创业者,起初看着很一般,脑子不算灵光,做事效率也不高。但在消费业务里,有时候运气来了,项目很快就有了正向反馈,这时候就会觉得人家还挺厉害。所以说,做投资真的急不得,耐心太重要了。

Harry 11:13
耐心,还有忍受痛苦的能力。实际上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是冥想应用程序 Calm 的创始人,他在我融资的时候跟我说:“听着,作为一个创业者,就是要有每天被打脸,还能说‘我会回来继续努力’的能力。”

完全正确。在消费领域你能看到更多情况,在企业服务领域看到的相对较少,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我不做 pro rota。我参与了 Hopping、Clubhouse、BeReal 等公司的投资,还有很多企业服务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发展速度慢很多,但都是非常出色的投资项目。你对 pro rota 和这种投资方式有什么看法呢?
David 12:05
我们第一支基金没设按比例跟投资金,后来发现问题了。有些公司发展慢,急需帮助,这和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没办法只能打破规则。
埃里克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是团队里最讲原则的投资人,为团队发展打下了不少基础。当时 Trade Desk 公司快没钱了,埃里克很纠结,他说:“要是咱们不投,这家公司就撑不下去了。” 对他来说,打破自己坚守的规则特别痛苦,但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就说:“必须投!”

Harry 12:50
那次跟投了多少钱呢?
David 12:52
大概在 50 万美元到 100 万美元之间,不管我们投了多少,感觉都不少。在第二支基金(Fund 2)中,我们制定了 pro rota 策略。
Harry 13:15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多需要 pro rota 投资项目,最后都血本无归(价值归零)。
David 13:26
是啊,我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制定了 pro rota 策略,规定如果投资后公司估值超过 2000 万美元,我们就不会投资。但后来市场发生了变化,你知道,这个规则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所以你制定了这些规则,然后市场变了,在某种程度上,两年后你就得根据市场情况再次尝试修改这些规则。
Harry 13:58
基金规模是 7500 万美元,所以你们是一比一的 pro rota 比例,假设初始资金是 3500 万美元(我是说,包括各种费用等等,所以初始资金是 3500 万美元)。天哪,如果你要投出 250 万美元的支票,数量也不会很多。
David 14:15
新冠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慌,感觉市场都快不行了,当时就想着得给投资的那些公司 “输血”。可后来发现市场上突然到处都是钱,大家都在搞日内交易,而且我们基金募集的时机也不太对。这让我们明白,在风险投资里,储备资金以及怎么管好这些资金,真的是太难了,想要做好几乎不可能。
Harry 14:48
这也非常困难,因为你得前瞻性地考虑投资组合未来的情况,而对于那些可能甚至还没有进行的新投资,这是非常难预测的。
David 14:58
每当我觉得我们应该多预留一些 pro rota 资金时,我几乎就感觉市场会变得疯狂。而每当我觉得我们应该少预留一些 pro rota 资金时,我又会想,天哪,市场好像马上就会让你意识到现在真的需要更多资金。
Harry 15:10
如果一家公司毫无进展,你对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也失去了信心。你会告诉他们吗?
David 15:25
我想我最好还是说点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什么都不说,那就是在逃避责任。就拿 Ti 公司来说吧,我们刚刚关闭了这家公司。这是一家从事碳捕获业务的公司,真的是在海洋中进行碳捕获,业务听起来不可思议。我们投了 1000 万美元,而他每个月要烧掉 300 万美元。我觉得马蒂(Marty)后来都不接我的电话了,因为他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说了。我给他发了封邮件说了这事。事实就是最后……
Harry 16:51
你觉得首次创业的创业者和有过重大成功或失败经历的二次创业的创业者,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David 17:04
一般来讲,那些成功卖掉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创业者,再遇到新机会时,往往会有些傲慢。我自己就是这样,卖掉第一家公司后,感觉自己干啥都能成。这种人看哪个领域都觉得能轻松征服,想给别人 “秀” 一手。但这种心态在投资里可不太妙。
反而是那些创业失败的人,再次回来时对成功的渴望特别强烈,一心想证明自己。要是还能把原来的团队拉回来,那就更厉害了。
汤姆・李创办的 Motorway 公司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之前在旅游领域创业,产品不错,可烧钱太猛,每个月花 1000 万美元,想跟凯悦竞争,最后还是失败了,把我们投的钱都亏光了。但他没放弃,重新拉起团队创办了 Motorway 公司,现在这家公司估值 10 亿美元,相当厉害。所以说,对我们投资人来讲,得让这些有潜力的创业者愿意回来找我们。

Harry 18:18
从这件事你学到了什么呢?
David 18:21
我想说,创业失败往往不是因为你和团队不够努力,你们工作又快又高效,只是当时环境太恶劣。如果失败了,别灰心,回来找我。
每次面对投资失败,我都更明白这个道理。我很看重团队,甚至超过项目本身。有的团队虽没成功,但我还是欣赏他们。我希望他们能回来,不是为了利益,只是单纯想和他们继续合作。
Harry 18:59
我特别赞同你的看法。有限合伙人总问个让我头疼的问题 ——“你看好哪个投资方向?” 我觉得这问题问得太敷衍了。在咱们这行,还有个偷懒做法,就是按比例跟投,好多基金都这么干,张嘴就是 “按比例跟投就行”。这做法看似简单,实则是在逃避深入思考。依我看,投资就得果断,要投就全力以赴,不行就果断退出。你怎么看呢?
David 19:23
我仍然觉得按比例跟投对创业者来说就像是一种“原罪”。
哈里,你之前问我创业者对风险投资有啥不了解的。打个比方,要是我对你说,给我 1000 万美元,让我有权按某个价格买 20 风险投资公司 10% 的股份,买不买还由我决定,你肯定不会同意,对吧?可很多创业者不明白,他们给投资人按比例跟投权,就类似这种情况。
创业者居然会给投资人按比例跟投的权利,这对风投来说是好事,对创业者却不利,相当于给自己挖坑。通常,后期风投会让创业者去市场询价,实则是自己不想定价。
Harry 20:30
为什么在公司苦苦挣扎的时候按比例跟投就糟糕呢?
David 20:31
当公司去市场融资时,要是股权结构里已经有像 XYZ 这样的长期基金,公司就像 “探路者”,其他人会参照它来给公司定价,这会让交易很难达成,除非公司特别成功。就像酷澎找红杉资本融资时,预估值 40 亿美元,贝莱德要投 10 亿美元,公司发展好时,原有投资者可能没法按比例跟投;发展不好时,后期投资者想要 20% 股权,原有投资者又要按比例跟投,最后创业者会发现股权稀释比预期严重。所以,不管公司发展状况如何,按比例跟投对创业者都不太有利。

Harry 22:40
你觉得还有其他哪些条款你认为是不合理的呢?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请过来自 Notation 公司的伊埃尔(Eel),他说过,我们应该接受普通股,也许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就像你说按比例跟投是很奇怪且错误的做法一样,还有其他你觉得不合理的条款吗?
Harry 24:11
你怎么看待市场和估值发生了重大变化?
David 24:29
公开市场变化巨大,2020 - 2021 年 SaaS 公司市盈率倍数有 20 倍,现在只有 5、6 倍,这种变化正影响一级市场。
Harry 25:15
我很认同这一点。如果公开市场的市盈率倍数不回升,酷澎(Coupang)公司能生存下来吗?
这问题问得好。我觉得投资实收倍数(DPI)可能没啥参考价值了,听我给你讲讲。很多有限合伙人在看 2018 年及以后成立的基金时,都盯着 DPI。但实际上,2018 年成立的基金(fund 3)到现在都还没产生 DPI。
对比一下,我们的第一支和第二支基金,运营五六年时就有 DPI 了,而且还不是靠最成功的投资项目,像克鲁斯、桌面自动化公司,还有第二支基金里的桌面金属公司,DataLot 和 Infos Scout 这些公司都贡献了不少。那时我们还没投资优步、Trade Desk 和酷澎呢,Seatgeek 和艾可表格也还没产生 DPI。
可 2018 年及以后成立的基金就不一样了,当时情况很特殊。我们投资了不少潜力股,结果 2019 -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大家都在家搞日内交易,投资比例变得很夸张,像 10 比 40、20 比 80 之类的。老虎环球基金看到 A16Z 这么投,自己就加大比例,软银也跟风,投资疯狂到了顶峰。
这样的情况下,有限合伙人,尤其是那些谨慎的,还是想投资优质基金。虽然他们不会直接跟基金经理说,但心里都在想:把 DPI 数据拿出来给我看看。
但是当有限合伙人(LP)向你要求资金流动性时,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说到流动性,我们该如何解决呢?因为我认为首次公开募股(IPO)市场最早也要到 2025 年才会开放,而且并购市场实际上也并未真正开放,不是吗?
David 27:56
是啊,你知道有句俗语叫“一燕不成夏”。但我却觉得,一只燕子也能带来夏天。所以乐观地看,一次成功的 IPO,大家就都会去上市。市场会再次开放。我认为目前美国的 IPO 市场基本处于关闭状态。我觉得选举之后,要是有一两家或三家出色的公司上市,马上就会有大批摩根大通和高盛的银行家跑来跟你说……
Harry 28:24
市场开放了。得有个像磁石一样有吸引力的公司,Instacart ( 生鲜杂货配送平台)可不行。
David 28:29
有很多市值 40 亿、50 亿、60 亿美元的公司,比如席特吉克(SeatGeek,票务平台)已经筹备上市两年了,但光靠一两家这样的公司还不够。不行,那可不够。
Harry 28:37
得有像 stripe(支付公司)那样的公司,得有个备受瞩目的公司,得有像 SpaceX(太空技术公司)那样的。对。
IPO 市场就会开放,我觉得一旦出现(那种公司上市的情况)就会开放。而且有限合伙人也会活跃起来,因为有很多有限合伙人在那些公司持有股份。
Harry 32:52
那么 LP 还在继续投资这个 VC 资产类别,实际上并没有撤资。由于缺乏流动性,有限合伙人的资金配置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David 33:02
这取决于这些有限合伙人是谁。比如捐赠基金。
Harry 33:06
还有养老基金,不过捐赠基金已经减少了投资,他们已经降低了投资比例。
David 33:10
他们确实降低了一点投资比例,但我觉得他们总会这样想,看,我们必须在风险投资领域配置 1%、2% 或者 3% 的资金,至少会配置更多。完全正确,确实是这样。如果你看看像斯旺森(Swanson)模式,风险投资的配置比例更像是 30%。
Harry 33:27
不过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就是他们都参照了斯旺森模式,然后想,等等,我们可以复制这种高达 35%、40% 的资金配置比例,但那是在流动性更好、项目筛选成功率更高的时候。现在你的成功率低多了,而且真的缺乏流动性。是啊。
David 33:46
嗯,所以,你也看到了,高净值家族办公室撤资的情况更多了。我觉得基金成立的年份真的非常重要,一些大型有限合伙人会对某些年份成立的基金有所顾虑。有点像 Accel 基金的第七期那个时候,你知道吧?所以我当时没参与投资,结果错过了对脸书(Facebook)的投资机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作为有限合伙人认为自己投资了一支优秀的基金,你可能会降低投资比例,但还是会尽量留在这个投资领域,不过你必须保持良好的投资记录。
Harry 34:11
你必须是一支优秀的基金。在那种情况下,你介意有限合伙人退出吗?
David 34:16
我们的基金规模很小,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欢迎有限合伙人退出,比如在我们的第五支基金里。我们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家族办公室,我们很喜欢他们,他们说如果投资金额低于 1000 万美元,他们就退出。我们说,你们的投资金额确实低于 1000 万美元,他们就退出了。我们的基金规模小,哈里,我们不介意。如果你问我,我花在基金募集上的时间非常少。说实话,我 95% 的时间都花在寻找优秀的公司和支持优秀的公司上了。我觉得我只花 3% 的时间在基金募集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心有限合伙人。我随时都愿意和有限合伙人交流,我也很喜欢和他们相处,但我不会专门去进行基金募集工作。
Harry 35:51
你提到过,那些从老虎基金(Tiger Global)、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ndreessen Horowitz)和软银(SoftBank)等机构那里融资,然后又进行了估值下调的公司。我们是不是即将看到它们被淘汰,会发生什么呢?
David 36:10
那些没能实现产品与市场契合的公司,迟早会被抛弃。董事会会逐渐放弃,公司内部也会士气低落。有些公司,哪怕已到发展后期,甚至已经上市,也难逃此劫。对于未上市的私营公司而言,要是市场不再青睐,即便手握大量资金,一旦烧钱过快,距离倒闭也只是时间问题。
要是公司业务始终不见起色,就别指望投资者一直不离不弃,这关乎双方关系。投资决策虽偏商业考量,但也掺杂情感因素。投资者和有限合伙人会转移投资目标。不过,要是我和创业者私交不错,相信他有能力扭转局面,哪怕这想法有些盲目和感性,我或许也会选择继续支持。
Harry 37:45
我们提到了库旁(Kupang),提到了优步(Uber),提到了贸易桌(Trade desk)。我很欣赏我们共同的朋友艾比(Abby)关于实际出售(公司股份)的框架,他在节目中把它分成了三个不同的部分。当你看到这些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时,我很好奇,你会在它们上市时出售股份吗?你进行清算的流程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有效地进行分配呢?
David 38:10
我借鉴有限合伙人、气象仪表公司首席投资官汤布利・姆普斯的观点来讲。在优步、库旁等项目中,分配股份时,汤姆指出,无论怎么决策都会有弊端:过早出售,会错失后期增值;一直持有,又可能保不住价值。
实际情况更复杂。部分投资者想把股份捐赠给基金会,若套现给他们现金,会招致不满;还有投资者对所持股公司不了解,希望代做决策。
通常,持仓量大、能影响基金走向,或分配股份达基金一半时,我们会进行分配;持仓量小的,在公司 IPO 时让投资者自行决定。比如 Desktop Metal 公司估值约 1000 万美元时,我们卖掉股份进行现金分配。我们主要依据股份规模与基金规模的比例做决策。
以优步为例,其股价涨了 25 倍,市值达 1500 亿美元。回顾过往,真想一股都不卖。虽说大家有生活需求,但对于有竞争壁垒的优质公司,最好长期持有,这就契合巴菲特的投资理念了 。
Harry 48:30
你觉得在当今如何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种子轮融资呢?因为我看到现在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种子轮融资竞争都非常激烈,而且估值也高得离谱。
David 48:40
我们(的投资策略)是反常规的,不随大流,坚持逆向思维。所以当我看到那些融资轮次时,如果我看到一个融资轮次是投资 500 万美元占 20% 的股份,这在我们的投资范围内。
但当我看到那些像是投资 2500 万美元占 1 亿美元(股份)的融资轮次时。我们基本上就不参与了。同样,还是团队和主题(投资方向)的问题。所以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看到某个人或某个项目,你会突然在早上醒来想到,天哪,我怎么能不参与呢?但在大多数情况下,99% 的时间里,我们都不会参与,因为在种子基金投资中,按照那些(高估值)数字,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赚钱。
Harry 49:12
这就好比 OpenAI 公司,我告诉你,我是最早一批在 OpenAI 公司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就接触它的人之一。它的第一轮融资我记得大概是 25 万美元。我说,这不可能(投资)。你当时写支票(投资)了吗?没有,我说作为一个种子基金经理,我不可能投资 25 万美元(到这样的项目)。结果它的估值涨到了 50 亿美元,而且还会有很多稀释(股权)的情况,因为我能得到什么呢?要是它成为一家市值 500 亿美元的公司呢?
David 49:37
是的,总的来说我很钦佩你的原则性。我觉得从后见之明来看,你不能基于后见之明来设立基金(投资策略),你可以想想那些你错过的项目,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每一代会出现一两家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司,或者也许一年才出现一家。如果你投资了这样的公司,那太棒了,但你能基于此制定一个基金投资策略吗?我觉得不能,至少对于种子基金来说不行。
Harry 51:30
你认为人工智能会催生一代新的、市值巨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公司,还是会让现有的大公司巩固其市场权力呢?
David 51:40
我觉得有短期和长期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从短期来看,我们现在可能会感到失望。我觉得如果你看看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的资本支出,再看看短期内实际能产生的收益,根本说不通。
Harry 51:53
大卫·卡尔(David car)说过,这是一个价值 6000 亿美元的人工智能问题,确实就是这样。
David 51:57
而且我觉得整个生态系统都是这样。所以不只是超大规模的企业(面临这种情况),对吧?就像大卫也说过的,从数据中心,到钢铁行业,再到芯片行业(都受到影响)。我觉得从短期来看,它会让人失望。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哈里,每一次这样的技术浪潮都让我想起自动驾驶汽车的发展历程。我记得和埃里克打过一个赌,他说自动驾驶汽车能在五年内实现吗?我对他说,最后 5% 的技术突破非常困难,而现在我们逐渐接近实现自动驾驶汽车了,所以这需要很长时间。
Harry 52:26
但突然之间,然后砰的一声,Waymo 公司(就取得了进展)。
David 52:30
拿 Waymo 来说,要是你在加利福尼亚坐过它的车,肯定会深感震撼。未来 10 年,要是还不重视人工智能,那可太不明智了,它必将带来深远变革。
可这领域竞争激烈,如同好莱坞,1000 家公司里可能只有 1 家能一飞冲天,100 家里才有 1 家表现出色,这吸引了大量资金涌入。我们很难确定哪一家能成为佼佼者。
我记得和埃里克参加年度晚宴时,一位有限合伙人悄悄凑到埃里克身边,好奇地问:“你们当初怎么知道优步会成功?” 埃里克坦诚地直视对方,回应道:“其实我一开始并不了解这家公司。” 人们总爱事后美化,夸大他当时的远见,可实际上,他起初也没把握,只是觉得优步有点意思,和对其他公司的初步印象差不多。
我们很难预判哪家公司会成功,不妨主动参与,关注优秀团队。至于到底该怎么做,我也没有确切答案。
Harry 56:54
如果判断失误,那为什么会失误呢?
David 56:55
所以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会想,我喜欢这家公司的业务,但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我真是吃了苦头才学到这一点。
David 57:03
科尔曼(Coleman)把他们分成了两类。他们是那种“红色按钮”型创业者还是“绿色按钮”型创业者呢?意思是,晚上 7 点,就在你要和家人吃晚餐的时候,你会接这个电话吗?嗯,如果是你(这样的人),我会想,我喜欢这个人,我会接这个电话,然后说,我吃完晚饭给你回电话。但如果是“红色按钮”型(不太好的创业者),那我就会犯错,我会看着电话想,我不想和那个创业者一起吃午饭或晚饭。
Harry 59:00
你觉得项目的热度和项目质量有关系吗?
David 59:02
不,一点关系都没有。是的。
Harry 59:03
这是我的看法,我回顾我们的投资组合,尤其是那些最热门的项目,结果发现最热门的五个项目和 25 个项目中,表现最差的就是那些曾经最热门的。
David 59:09
实际上,在理想的情况下,如果一个项目非常热门,而我们又很早就参与了,如果你能进行二次出售,那就是个很好的时机。有时候可能做不到,但我整天都在和团队讨论这个问题。
Harry 59:56
你最后悔卖掉哪一家公司的股票呢?
David 59:58
嗯,我后悔卖掉了 The Trade Desk 的每一股股票,我也后悔卖掉了优步的每一股股票。事后诸葛亮总是最准确的。这些都是有强大护城河的公司,为什么要和它们作对呢?
Harry 1:00:09
你提到了二次出售。在过去几年里,创始人因为进行二次出售而受到指责。
我对那些成长型投资者很生气。他们在行情好的时候把大量资金塞进创始人的口袋,后面行情不好,他们却又说,我真不敢相信这些创始人把那么多钱套现了。
David 1:01:44
是啊,我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上一个时代最大的罪过就是涌入了大量资金,简直是海量资金。
我们投资的 Oda 就是其中之一。但现在回头看,你会想,那些创始人怎么知道该怎么用那些钱呢?他们拿到了那么多钱,如果没有那些钱,他们可能不会在美国扩张业务。但你看,你在美国开了一家办公室,而你的商业模式在英国还没完全成熟呢。所以说,上一个时代的罪过,就是那些海量的资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罪过。
Harry 1:03:21
但我实际上觉得情况并没有改变太多。
David 1:03:24
我觉得现在情况正在改变。如果你是一家年收入 5000 万美元的垂直软件即服务(SaaS)公司,上市后的估值倍数会限制你。你不可能得到 20 倍的估值倍数,兄弟,因为我持有股份的那家上市公司的估值倍数只有 6 倍或 7 倍,就是这个倍数。
Harry 1:03:45
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因为你说得太对了。但这意味着所有人都有点想退出垂直 SaaS 领域,觉得这个领域不吸引人了。
David 1:03:52
有意思的是,这又回到了安德烈森(Andreesen)的观点,你知道的,安德烈森说过,软件正在吞噬世界。你看看一些垂直 SaaS 公司或水平 SaaS 公司,它们拥有海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像 Salesforce 的马克·贝尼奥夫(Mark Benioff),如果你忽视他的公司,那你就危险了,因为他们拥有的数据量非常大,他们引入这些人工智能工具,开展自己的业务,对吗?他们的机会是巨大的。我在我们投资的一些垂直 SaaS 项目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如果我们给客户提供丰富的数据,要是我们不丰富数据,我们就会失去业务,但我们丰富了数据。然后你回头看,你会想,就人工智能而言,这到底是谁的机会呢?如果你拥有数据却没把握好,那只能怪你自己。
Harry 1:04:37
人工智能是不是意味着你可以提高每个用户席位的收费价格,还是说只能维持现状,甚至会降低利润率呢?
因为我请了 Canva 的首席产品官参加节目。他说,哦,我们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做各种了不起的事情,我觉得这很棒,但他提到了每次查询都会涉及的利润率整合问题。然后他们宣布价格上涨 300%。Canva 是一款很棒的工具。我相信人们会为此付费,这很好,但我们是会看到价格上涨呢,还是利润率提高呢?
David 01:05:11
我认为短期内要采取防御策略,短期内要采取防御策略。如果你完善了业务,而且是你做到了这一点,并且你留住了客户,而且由于业务的完善,你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客户群体。看看那些伟大的公司,比如特斯拉,要不就看看网景,对吧?在某个阶段,免费增值模式(freemium)被发挥到了极致。我认为合适的做法是一开始先采取防御策略,然后一旦你留住了那些客户,并且丰富了数据。
Harry 01:05:37
有投资人说人工智能意味着公司将能够根据自身特定需求构建自己的垂直解决方案,并且从这个角度来说,垂直软件即服务(SaaS)行业将会终结。
David 01:05:51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实际上一些工具已经非常商品化了,垂直 SaaS、水平 SaaS 或者数据所有者在某个时候将能够以相当低的成本使用那些基础工具。你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认为如果你看看围绕这方面的一些开源软件,那些基础工具会越来越商品化。所以你可能会说,嗯,为什么不是每一家公司都能做到呢?我觉得不是每家公司都能做到,但我认为会有一些软件提供商完善他们的工具集,并且会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成绩。
Harry 01:06:20
我认为我们大大高估了这些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构建自己的垂直解决方案的技术成熟度,他们连 Slack 的上手使用都很困难。
David 01:06:34
这让我想起了我和我的合作者创办 RISP 的时候,我们去找了最大的几家银行,向他们提供互联网服务、托管服务以及各种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然后我们又去找了类似国家铁路公司这样的企业,他们说,看,我有自己的网络,我拥有一个网络。我的每条铁路上都有光纤。我拥有的网络规模比你们的大得多,我自己能做所有这些事情,我为什么需要你们呢?我记得当时就想,好吧,那就走人,对吧?六个月后,他们什么都没做,一年后也没做,两年后还是没做。答案是,短期内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又会说,我不需要你。
那么,从智能软件解决方案的角度来看,有商机吗?有,而且商机仍然无处不在。
Harry 01:11:19
关于风险投资领域,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我们还没讨论但应该讨论的事情呢?
David 01:11:23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刚刚在这里写下了“媒人”这个词,比如小型基金和大型基金的区别,还有那种大型基金,也就是长期投资者基金,它们实际上没有动力为你牵线搭桥。它们有自己的考量。
作为小型基金,我们不会持续多轮投资。我的主要工作是牵线搭桥,像个高级媒人,给创业者介绍其他投资者。
这和红杉资本这类机构有很大区别。红杉拿到投资份额后,不会帮创业者对接其他投资者,一心只为自身利益,本质就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者。如今很多风投都这样,市场热门时按清算价投资,不热门就不投,如同做看涨期权交易。
但种子轮基金不一样,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创业者获得资金。过去 15 年,我们把对接流程优化得像软件一样。公司安排专人借助 Airtable,帮创业者找到最合适的投资合作伙伴,堪称超级加强版媒人。
Harry 01:15:00
你怎么看到 TAM,目标市场总规模?
David 01:15:04
我们做(投资)时会考虑市场规模。我见过很多次,投资者会看目标市场总规模(TAM),然后放弃一笔交易,他们会说,因为目标市场总规模不够大。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 Media Radar。我和贝恩资本预备基金(Bain Capital Prep)、芬德联合(Fender Collective)一起参与了这家公司的投资。如今,它即使不是全球媒体领域最大的垂直软件即服务(SaaS)项目,也是最大的项目之一。
Media Radar 如今估值达十亿美元,真希望当初没退出,创始人是托德・克里萨尔,公司非常出色。我们曾把它介绍给贝恩飞桥资本、贝西默。我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贝西默团队做了市场规模评估,他们认为报纸和杂志行业在衰落,依据目标市场总规模的概念,这一观点很难反驳,我作为天使投资人也觉得这个行业市场规模也就几亿美元,而非几十亿。
后来,Media Radar 拓展业务,涉足脸书、谷歌、网飞、苹果、亚马逊等领域,所有在线和屏幕展示业务都有它的身影,目标市场总规模变得近乎无穷大。由此可见,当初严重低估了目标市场总规模。虽然这一概念听起来诱人且合乎逻辑,但公司刚起步时,目标市场总规模并非那么关键 。
Harry 01:16:22
实际上,我也真的这么认为。我认为价值 10 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与价值 100 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之间的区别,或者说价值 10 亿美元的公司与价值 100 亿美元的公司之间的区别,在于一个真正伟大的创始人,真正优秀的创始人会去开拓市场。
David 01:16:42
我同意。我认为,从后视镜视角(事后回顾)来看,当我们比较德励(The Trade Desk)和奥乐科技(Olo)时,你会发现,德励的目标市场总规模几乎是无穷大的,对吧?它简直可以和谷歌、脸书以及德励自身相媲美。然后你再看奥乐科技,你会想,好的,垂直软件即服务,餐饮行业,它的目标市场总规模可能有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但事实就是这样。
Harry 01:17:09
我想和你进行一个快速问答,我说出一个简短的陈述,你立刻告诉我你的想法。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你改变想法最多的是什么事情呢?
David 01:17:19
我过去认为私募股权(PE)公司是种子轮投资阶段的敌人,但我现在改变了这个想法。我参与的两家垂直软件即服务公司引入了一些私募股权公司。他们的严谨态度、财务纪律,以及他们给予那些公司的帮助,对整个资本结构表都非常有益。所以私募股权公司对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来说可能非常、非常有价值。
Harry 01:17:42
下一代的流动性将由私募股权公司提供,你认同这是核心观点吗?
David 01:17:48
完全认同。
Harry 01:17:49
你最想和哪位投资者交换投资组合呢?
David 01:17:53
我觉得从公司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更容易。所以如果我想到应用人工智能领域,想到一些相关公司,我就会想到微罗森布鲁姆(Micro Rosen Bloom)的 Vocata 公司,它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摄像头领域的。还有乔希·沃尔夫(Josh Wolf),他从勒克斯资本(Lux)出来后创立了安德鲁(Andrew)公司,该公司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无人机领域的。同样,如果我看看乔希·库什纳(Josh Kushner),他投资的公司价值从 10 亿美元到 100 亿美元,我不会和他打赌(认为他会失败)。所以是这些公司(让我想交换投资组合)。
Harry 01:18:15
在你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公司里,哪位董事会成员最出色,原因是什么呢?
David 01:18:18
来自安佰深(Emergence)的杰克·萨伯(Jake Saber)在 Regal 公司(担任董事会成员),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助力者,是公司非常棒的合作伙伴。杰克为安佰深找到了 Zoom 公司,他功不可没。他扭转了这家投资组合公司的局面,在每一次招聘、每一条建议方面,他简直是为公司竭尽全力,在公司发展的后期阶段也是如此。他选择(参与的项目)非常谨慎,他不会参与太多项目,但当他参与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全身心投入。你收到过的最好的投资建议是什么?要有耐心,保持耐心就好。
Harry 01:18:53
你现在知道的哪些事情,是你希望在创办 Founder Collective 时就知道的呢?
David 01:18:56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甚至在公司上市之后也是如此。当你认为你的公司有真正的护城河,很难被竞争时,要坚持住,不要出售(股份),不要过早出售。
Harry 01:19:07
你最大的投资损失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David 01:19:09
我遇到马蒂·阿德林达(Marty Adlinda)时,他正准备创办 Running Tide 公司,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是他们家族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也是我在应用海洋领域遇到的最有想法的人之一,他是第三代龙虾渔民。我当时被他深深吸引了。我认为我低估的是将产品愿景转化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东西,这并没有实现。我们在 Running Tide 公司的投资血本无归。
Harry 01:19:48
零利率政策(ZERP)时代最大的罪过是什么?
David 01:19:50
就是资金太多了,一切都被资金驱动,太多的资金被硬塞给创业者。
Harry 01:19:56
但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人生中最沉重的东西不是铁,也不是金子,而是那些未做的决定。哪个未做的决定让你最耿耿于怀呢?
David 01:20:26
这问题问得好。回顾过往,重大决策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都需要权衡利弊。让人们坚定信念很难,大家总以为重大决定是毫不犹豫做出的,可实际上,很多重要决定,往往只有 51% 的把握。
拿我来说,离开南非回波士顿和埃里克创办 Founder Collective 公司,一方面和埃里克共事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却要背井离乡,抉择极其艰难。而且人越年长,越难做出非此即彼的决定。
作为投资人,向创始人出具投资意向书,提出进入董事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也并非把所有问题都考虑周全了。做决定时,情感和理智常相互拉扯,有时就得跟着感觉走。
比如和创始人沟通后,我离开时充满干劲,回家睡一觉,又会担忧失败,上班路上、工作时不断自我说服。有时对创始人的好感来自情感本能,忽视这种感觉,同样可能犯错 。
写在最后
除此之外,其他相关文章请阅读,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投资建议,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